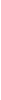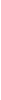列祖列宗在上 - 第156章
顷刻间,数名黑衣死士从船舷两侧无声涌出,刀光映着冰冷江水。箭矢从刁钻角度不断射来,一名暗卫闪避不及,闷哼着跌入漆黑江面,再无声息。
费电目眦欲裂,挥刀格开迎面劈来的利刃,水战本非京都暗卫所长,在这摇晃的船上,他们身手受限,敌人却如履平地。
刀剑碰撞,火星四溅,费电肩上多出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,他喘息着看向近在咫尺却如隔天堑的主舱门,心头渐沉。今夜救出沈菀已无可能,若能带着兄弟们全身而退,已是万幸。
船舱内,沈菀听着外面隐约传来的厮杀与利刃入肉声,脸色苍白。
可所有的忐忑不安在对上赵淮渊执拗的眸子时,又悄然溃散,她坚定的伸出手,这次不再是推开,而是更紧地环住男人紧绷的脊背。
“怎么,不打算逃了?”赵淮渊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疯癫,他似乎又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意识了。
沈菀叹息:“不了,我就留在这里,守着夫君,哪里都不去。”
此后一连数日,试图救人的暗卫彻底没了踪迹。
秦淮河的夜幕依旧声色犬马,千盏花灯在水面投下摇曳的光影,将河水染成金红。靡靡笙歌从画舫中飘出,与岸边小贩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,交织成这座不夜城独有的繁华。
纵然知道这些烦人的奴才不会善罢甘休,赵淮渊也丝毫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。
沈菀倚在画舫栏杆旁,眼前仍是一片漆黑,却依旧能感受到暖风里裹挟的热闹气息——脂粉香、酒气、糖糕的甜味,还有水面飘来的湿润。
赵淮渊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,仅剩的一只手虚扶在沈菀腰侧,像是怕她跌倒,又像是怕她逃走。
“夜夜笙歌,当真是热闹。”沈菀微微侧耳,似乎沉醉在此刻的热闹中,“就连江南的小曲儿,都比京都的软腻些。”
赵淮渊指尖在她腰间轻轻一收,将人拢进怀里:“你喜欢?”
“嗯。”沈菀顺势靠向他,唇角弯起温柔的弧度,“若是往后日日都能同渊郎在这里,听听曲、看看灯,该有多好。”
他低笑,下巴轻蹭过她的香腮,气息温热地拂在她耳际:“知道你在哄我……可我听着,还是欢喜。”
沈菀没说话,只将脸贴向他胸口,心里却轻轻叹息——她在赵淮渊这儿,怕是早就没什么信誉了。
也罢,日子还长。
恰逢一艘华丽的花船从他们的画舫旁缓缓驶过,船头还立着几位身着轻纱的歌女,正随着乐声翩翩起舞。鬓角的珠翠在灯火下摇曳,衣袂飘飞间带起阵阵香风。
沈菀忽然转过身,手指攥紧赵淮渊的衣袖,“淮渊”她声音软了下来,像裹着夜风里的缱绻水汽,“你小时候,常来这儿吗?”
沈菀这话问的突然,可娇嗔的调子里似乎透着无限的
期待,赵淮渊心头蓦的一紧,随即泛起紧张。
沈菀从不会无故问起他的往事,大抵是白天为难了她的暗卫,她又在暗暗找机会报复折磨他。
赵淮渊对此并不抵触,他习惯她的一切,哪怕是带着仇恨的亲近。
男人沉默片刻,是甘愿、亦是投降,主动揭开年幼时的疮疤:“嗯,我母亲曾是这条河上最负盛名的歌伎,光顾过她的恩客没有一千也有八百。”
沈菀微微睁大眼,失明的瞳孔映着灯火,漾开一层朦胧的波光。这是赵淮渊第一次向她提起过去——她心口涌起陌生的激荡,迫切地想触及他深埋心底的过去。
“她是个什么样的姑娘?”沈菀小声试探,指尖无意识地蜷了蜷,“定是世间极美的女子,否则怎会将渊郎生得这般好看。”
赵淮渊轻轻的吐纳着憋闷在胸口的情绪:“……”就连沈菀说的假话也像裹着牛奶和蜜糖一样,动听撩人。
“我阿娘远不及菀菀,是个愚蠢透顶的女人。”赵淮渊的声音里带着沈菀从未听过的落寞,甚至是柔软,“她总是幻想着某个一夜风流的恩客能带她走,结果就是一次次被利用、抛弃,最后还因生下我,惹来了杀身之祸。”
他顿了顿,语气又悄然间变得麻木:“之后,我便被姑姑带去了永夜峰。”
“奚寒衣……”沈菀至今想起寒衣阁主怨毒的眼神,还忍不住想咒骂一句疯女人,“她待你好吗?”
“我不知道什么是好,什么是不好。”赵淮渊的答案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,“他们既想用我杀人,又时时防着我。这世上我遇见的所有人,待我皆是如此。”
没有愤怒,也无怨怼。他天生就在这般利用与猜忌中长大,早已将这一切视作呼吸般自然。
只是在这麻木的陈述后,赵淮渊的语气忽然轻了下来,像悄悄触到什么易碎的梦:“除了菀菀。”
“菀菀是第一个说……要照顾我一生一世的人。”
“菀菀待我很好。与他们不同,与所有人都不同。”
沈菀的手指顺着他的衣袖上移,轻轻握住他的手腕。
掌心下,他的脉搏跳得比平时快——几番生死浮沉,难为他在此刻提起过往,心头还会为她泛起这般悸动。
沈菀心头忽然涌起无限的懊悔。
她该对他更好一些的,少年的赵淮渊像只丧家之犬,满身狼狈的闯入她的世界,只可惜,她的凉薄与多疑,终究让她错过了这个男人最值得被好好捧在心尖的年月。
“我想象不出你小时候的样子。”沈菀轻声道,声音里浸着难以言喻的遗憾,“一定很惹人疼……终究是我没这个福气。”
赵淮渊骤然收拢五指,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她的腕骨。沈菀轻轻“嘶”了一声,眉头微蹙,却并未挣脱,任由那片肌肤在他掌下渐渐泛出淡红。
“沈菀……”男人字字句句,试图割开暖昧的空气,“不必这般故作痴缠,这根本就不是你。”
他逼视着她,眼底暗潮汹涌,“纵使你不施手段,我此生也困在你掌心,翻不出去了。”
沈菀抬起眼,长睫如沾湿的蝶翼,簌簌轻颤,眸中漾开的情思,真切得令人心尖发颤。
“渊郎是怪我太过急切了么?”她声音软下来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,“抱歉,我只是……只是怕极了。怕你再不肯信我,怕你心里那道坎,我今生都越不过去。”
她任由身子软软地依偎过去,额头抵上他紧绷的肩线,吐息拂过他颈侧:“往日是我瞎了心,蒙了眼,将渊郎的真心践踏尘土,如今每每想起,都恨不能剜出这颗满是悔意的心给你看。”
赵淮渊不信,但是却又舍不得扫她的兴致:“太后娘娘身份尊贵,难得愿意花心思跟奴做戏,都随你。”
沈菀轻轻叹气,任由娇软的身子依附上强壮的躯体,将额头轻轻抵在他肩上,娇嗔的讨好:“渊郎,是我从前不好,是我狼心狗肺,伤了渊郎的心,今后,再也不会了。”
突如其来的亲近,声情并茂的剖白,一切都让赵淮渊觉得如此不真实,他的喉结忍不住滚动着,眼眶不受控制地灼热起来。
他试图仰起头,将那股酸涩狠狠逼回眼底,却仍有湿意悄无声息地滑入鬓角。他恨自己这般不争气,恨自己明明历经背叛与痛楚,却仍在她的三言两语下兵荒马乱。
沈菀看不见,自然也不知道他无声掉落的泪,只管拼尽全力的弥补,甚至是不惜一切的讨好。
“渊郎是这世上顶好的男子,”沈菀的声音很轻,落在赵淮渊的耳畔却是那样的振聋发聩,就连周遭喧闹的鼓乐声在她甜言蜜语的衬托下,都变得黯然失色,“……渊郎自幼就是个娇俏的郎君,我初见第一眼便爱慕极了……感谢老天,让渊郎还活着。”
赵淮渊这辈子还没听过如此多的甜言蜜语,往昔他耗尽力气在沈菀那里讨不到半句,此刻像是八月的急雨一般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。
男人的呼吸乱了。
他败了。
又一次丢盔弃甲,又一次狼狈溃逃。
沈菀嫣然一笑——十多年过去,怎么还是如此好哄。
水面倒映着画舫流光,丝竹之声未歇,方才的温存甜腻尚未在空气中散尽。突如其来的巨响,将一切美好冲散。
“轰——”火光冲天而起,瞬间映红了半边夜幕,华美商船已化作巨大火把,噼啪爆裂声不绝于耳。
“是顾十三娘的船!走水了!”岸上的惊呼声与奔逃声骤然掀开,方才的靡靡之音被恐慌取代。
赵淮渊立刻警觉起来,转身就要唤人,沈菀等的就是这一刻,她手腕一翻,袖中一抹冰凉悄无声息地滑出,细若游丝,在灯火下几不可见的金线,带着惊人的柔韧与精准,瞬间缠绕上赵淮渊刚刚抬起欲唤人的手腕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